Brows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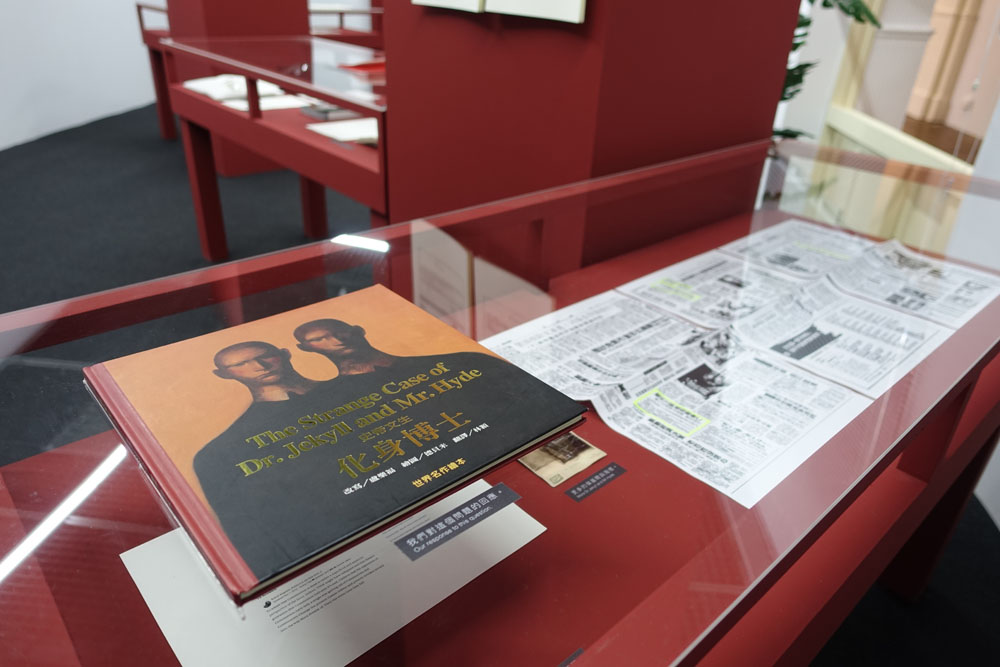
現今席捲全球,讓人又愛又怕的的區塊鏈、大數據和人工智慧等數位科技、許多國家與地區迄今仍揮之不去,並且讓人既無感、又有感的(後)殖民幽靈,以及在(後)殖民幽靈仍揮之不去的情況下行使的、不可能的轉型正義這三個當今世界最迫切的事件之間有任何關係嗎?如果有關係,三者之間的關係為何?我們該如何看待這些關係?由黃建宏策劃,8月4日至10月21日於台北當代藝術館展出的《穿越正義:科技@潛殖》(Trans-Justice: Para-Colonial@Technology)極精彩地思考了這三個問題。首先在論述結構上,這個展覽給出的是一個由學理概念的微分化(differentiation),以及因為對「正義」的鬥爭所導致階級對立的共同化、共通化和再次感性分享。
Hello!我的名字叫做科技
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正義的問題在今天已表現為一種佔位的問題。口口聲聲要(對過去的舊政權)行使轉型正義的政治團體的信用破產,和對一小撮既得利益者利益的鞏固催生了許多對此心知肚明的「鄉民」及其諸如人肉搜索和遊戲性正義等新型態的類政治實踐。在這樣的狀態下,對各種必須的數位科技應用和操作,反而極吊詭地成為分歧和衝突的目標、利益、傾向和慣習的階級和群體之間的最大公約數。我們看似那麼不同,但又那麼相同。新舊政權之間交疊更替、真相還原、補償、懲處和重新分配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被一種充滿張力,且極為飽和的(數位)科技影像實體或「滿影像」(full image)取代—彷彿這個滿溢的影像實體就是「正義」。對一般百姓而言,歸根究柢屬於「人和人」之間的正義問題也被一種科技問題,或被科技中介的影像或「畫面」問題所取代。
就此,作為展覽名稱的《穿越正義:科技@潛殖》其實是這個問題的懶人包。這個懶人包透過email所屬的「網域命名系統」(Domain Name System, DNS)告訴我們:如果email在今天仍是分處世界各地的人們常用的那種與類比媒介最相似、最正統,因此也最政治的媒介的話,那麼申請並使用某家數位服務業者的email這件事,就意味著對某種「潛殖」、「潛殖關係(或經驗)」的隸屬,以及透過這種隸屬—這種對策展人黃建宏所說的虎假虎威和微法西斯式的「生態個體」(eco-individual)的製造—對自身進行的命名和分化。很卑微地,「我的名字叫科技」(反之亦然,「我的名字叫潛殖」),如此對轉型正義場域的既得利益者和數位服務業者的雙重隸屬就是我的身份和我的命運,而我只能在玩手遊、上臉書和在PTT上推文時以想像的方式獲得穿越正義,重拾那已佚失的「完整的生命」,像重新接關般地重新成為「完整的人」。
不過這只是展覽命名和論述結構的第一層意義。透過域名系統的使用、對「潛殖」這個數位服務業者的email的申請使用、將自己的email命名為「科技@潛殖」、在「穿越正義」欄位輸入自己的email並寫下郵件內容這一連串的隱喻還彰顯展覽的第二層意義,即任何一個數位物件、數位系統和數位服務在偶然(突發事件)和必然(邏輯)上,都是某個「國家」或「地區」的「人」的「人造物」(artifacts)和「政治產物」(political products)此一事實,即穿越正義的第二層意義在於「穿越穿越」或「穿越遊戲的穿越」,意識到任何形式的國內、國際政治和數位政治,在本質上都還是人的政治和主權政治。面對這種「以數位科技方式代入的潛殖」和「仍須穿越的『穿越正義』」,我們必須在國內層次上將「都使用相同的數位服務,但因正義問題而分歧和撕裂」的集合獨體(collective individuals)加以一致地共同化和相互地共通化,並嘗試構建新的數位物件、數位系統和數位政治。這正是這個展覽在名稱和論述結構上的賭注與挑戰。
從身體圖式、中陰影像到反思影像的套疊結構
而在展覽所涉的第二層次即作品內在的感性結構上,它則呈現出從身體圖式(corporal schema)、中陰影像(bardo image)到反思影像的「套疊」(mise-en-abyme)結構。首先,一進展場一樓展示臺灣哲學暨政治家鄭南榕手寫筆記字卡的OA檔案櫃、張紋瑄所陳列不無戲謔的自殺炸彈客著作、報章雜誌記載、詮釋性文本的檔案櫃和「國際自殺大賽」、徐坦所展示的羅馬法典、水上人家影像和自明的土地邏輯、咸良娥的〈未定義全景〉對現代社會種種應然、實然和科層制所做的肉體還原、吳其育的〈反覆驗證〉對人工智慧之諧擬性「再驗證」,以及白雙全在雨傘運動後,於法庭進行的「再身體化」及由此所有意無意帶出那個像蛇和「黑河騎士」一般的黑團塊,給出的是一個得以將人世間所有應然和實然的表象和現象予以還原,或更精確地說,予以「實體性還原」或「社會性還原」的身體政治。這個身體政治是汽機車的喇叭聲、眾人圍觀、呼喊和飲酒作樂的喧囂鬧嚷、似乎還在耳邊作響的炸彈爆炸聲和看著機械手臂寫著字句,聽著機械唸著擬好的腳本的「機械式個體」(machinic individuals)。

到了二樓,黃邦銓透過蒙太奇對母體進行的追憶和體現、黃漢明(Ming Wong)的〈明年〉(Next Year)對殖民情境中缺席的政治主體和政治想像的仿造、致穎和格雷戈爾.卡斯帕(Gregor Kasper)那有如「有聲默片」般的帝國殖民諷刺劇和解殖的身體政治、卡戴.阿提亞(Kader Attia)對「幻肢」現象的研究以及由此而生的對現代人與早已作為自身「器官」或「義肢」的數位物件之間的關係進行「修復」(repair)的可能、陳界仁的〈十二因緣—思考筆記〉、〈星辰圖〉和〈中空之地〉透過殘響、回聲和無肉身的塑膠感建立的那得以破除任何二元對立,且極為直白的「空間—邊界」方法和「老百姓邏輯」、法洛奇(Harun Farocki)的《平行 I-IV》(Parallel I-IV)對電腦遊戲的新建構主義(new constructivism)與本能和直觀性空間進行的演示和分析,呈現出在獨體與獨體間摩肩擦踵的實存情境已經回不去,只剩下摸不到肉的平滑塑膠感的情況下,由獨體的表皮與他日常接觸的各式各樣沒血沒肉的表象加乘和牽連出的那既未生,也未死的「中陰影像」
換言之,那些在刻意製造的(後)殖民情境中搔首弄姿的人物、揣想祖父經歷的幻視、對幻肢的想像性體驗、在監視器螢幕下的殘破肢體和「不完整的人」,和隨著玩家的操控而移動的電腦遊戲畫面都是這樣的中陰影像。就此,如果說一樓身體圖式的政治以咸良娥的〈未定義全景〉為完美例證的話,那麼,二樓的中陰影像無疑是由陳界仁的〈中空之地〉,還有正在觀看法洛奇的〈平行I-IV〉時邊可以聽到的〈中空之地〉的臨演們的呼聲「名字沒了,該怎麼辦?」。於此,我們看到展覽名稱與展覽作品主題之間的同一性,或《穿越正義:科技@潛殖》的套疊結構:在以「潛殖」為「集用池」(pool)和網域名的陳界仁的〈十二因緣—思考筆記〉、〈星辰圖〉和〈中空之地〉中,陳界仁的兄長也跟著成群結隊唱著客家山歌的婦女重回人世,邁向以(數位)「科技」為主導,或以(數位)「科技」作為個人事業及成就象徵的那似活非活的電玩世界,以及由此而來,由策展人和參展藝術家共同提示已竟和未竟的「穿越正義」。最後,配上黃以曦的展演,高達(Jean-Luc Godard)的〈東風〉(Le Vent d’est)和克里斯.馬克(Chris Marker)那極具未來感和預言意味的〈2084〉錄像,《穿越正義:科技@潛殖》如同〈中空之地〉最後從陳界仁兄長的面前步過,唱著客家山歌,向他重新指著往人世間的路的婦女一般,接引的是一條從活人的身體圖式、未死未活的中陰影像到展覽作品的反思影像之間來回往返,名叫「正義」的救贖之路。其所救贖的不是別的,正是因正義的失落而留下的一個沒有過去的過去、和一個沒有未來的未來。
奇觀挑戰下的穿越正義
在觀眾主觀的感知結構上,展覽也存在「對奇觀批判的批判」這個挑戰。換言之,雖然台北當代藝術館的前身是與「殖民」議題有關的日治時期專供日本子弟受教育的「建成小學校」,且雖然策展人黃建宏老師不斷以「獨立書店」的隱喻對這個展覽,以及以「書」的隱喻對參展作品進行提示,但在部份涉及台北當代藝術館的場地限制的情況下,這個展覽給出的還是一個洪席耶(Jacques Rancière)於〈影像的政治〉(Politics of the Image)和〈奇觀批判的批判〉(Critique de la critique du spectacle)一文中所說的「表象—真實」的二元對立結構。換句話說,對於並非擁有十分充足之當代藝術知識,且對科技、殖民和轉型正義議題並非有相當深厚之認識的一般觀眾而言,參展作品或「書」的獨特性終將被某種在外觀上同一或同質的「通道」式經驗所取代。而進出且穿梭於各展間的那獨一無二的「神秘屋」體驗,也終將被走出展館那熟悉的慣常體驗所稀釋。這不但是對奇觀社會的批判為何最後仍將失敗的關鍵,也是洪席耶提醒我們不該再有意無意深陷傳統「表象—真實」的二元對立模式,而該思考如何在「表象旁建立另一個(政治性的)表象」,或在「感性分享旁建立另一個感性分享」的最大原因所在。就此《穿越—正義:科技@潛殖》中的「科技」其實絕非「不明顯」,而是俯拾即是。值得警惕的反而是在「理工盲」或「科技盲」的狀態下,將「科技」獨立出來,視其為絕對超然、中立、新穎和透明地獨立於殖民和轉型正義等陳舊、骯髒的政治事務之外運作之物導致的無益區辨和不知所云 (註1)。作為當代「(轉型)正義—(後)殖民—(數位)科技」這三個極為重要的議題上行使的極為必要、迫切且有意義的槓桿,作為對這三角進行的轉動和連結,這個展覽對於一般觀眾的施力點、力矩和力道究竟何在?這恐怕是以任何形式實踐的「穿越正義」,在這個奇觀時代的最大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