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owse
吳庭寬:談一下妳是怎樣的人?有非官方的自我介紹嗎?
努拉伊妮.朱利亞斯杜帝(Nuraini Juliastuti):我是一個母親、作家、研究者與文化行動者,工作與研究領域涵蓋替代性的文化生產、東南亞藝術史、音樂與聲音、語言政治等。1999年我在日惹創立了Kunci,而最近剛從荷蘭萊登大學取得博士學位,我的博士論文是〈公眾:當代日惹的音樂與文化管理(Commons People: Managing Music and Culture in Contemporary Yogyakarta)〉。我現在常居於澳洲墨爾本,並跟我的丈夫富勒(Andy Fuller)合力經營一個藝文平台「Reading Sideways Press (註1)」…這樣好像還是太「官方」了。
吳庭寬:為什麼離開妳生長的泗水(Surabaya),還在日惹創立Kunci?
NJ:如果當時沒有離開泗水,我現在可能不會在此。雖然我生長於泗水,家人也都在那,但我並不喜歡泗水。1990年代初期的泗水太工業化,文化上近乎乾涸。我在泗水Airlangga大學社會系讀了一年,但一直感到校園生活有所欠缺,我想我可能不適合繼續待下去。1994年我轉考進加查馬達大學(Universitas Gadjah Mada, UGM)。進了加查馬達,我加入學生媒體,並開啟我反抗新秩序政權(Orde Baru, Orba)的運動網絡。在日惹我還讀了很多書,我很享受學校圖書館跟各種非政府組織的藏書。總之我得以接觸知識、思想得以開放,都從這裡開始。1990年代末期日惹的學生運動與藝術行動非常活躍,Kunci與許多社群都從當時起家。
WT:你長期在澳洲,怎麼跟印尼或Kunci的夥伴維繫關係?
NJ:Kunci目前有二名成員長住國外,但我們還是維持密切的聯繫,至少每週視訊一次。其實一開始大家並無這樣的共識,各自忙著各自的工作,後來有次我感覺Kunci怎麼好像空了,才跟大家討論團隊如何保持互動。後來成效不錯,至少我們能知道在彼此最近讀了什麼書、在做什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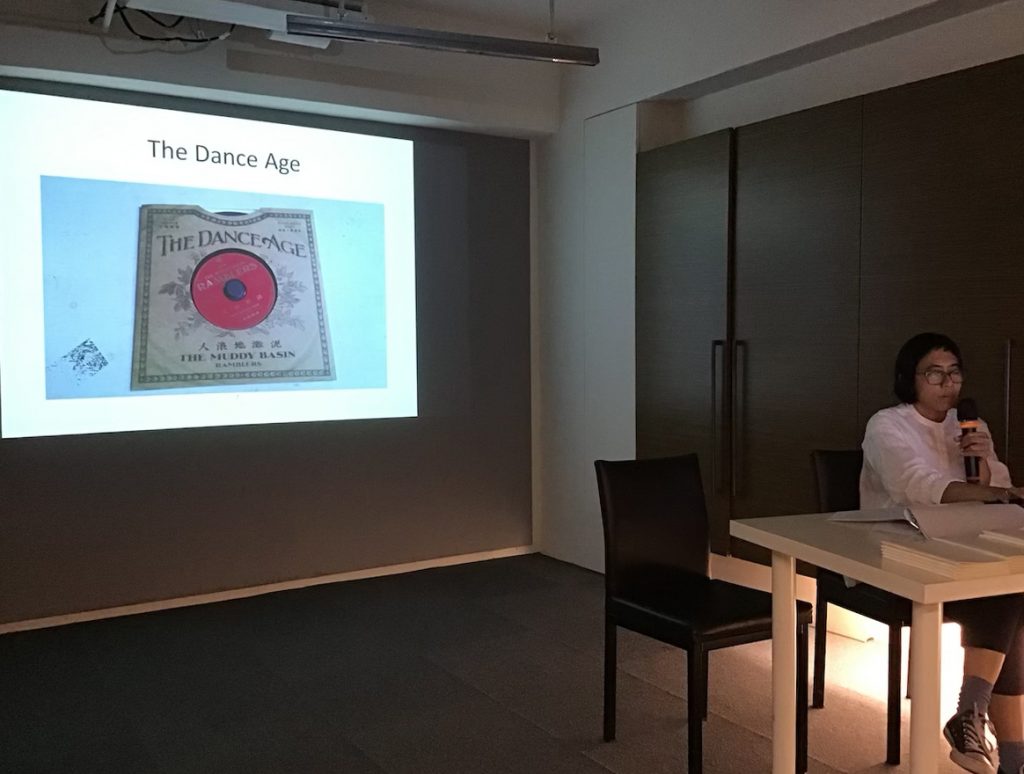
WT:印尼藝術圈對於題材似乎存在某種喜好,諸如環境、人權、社會少數等普世的當代議題,而許多重要的藝文機構也的確仰賴國外資金與網絡。藝術圈對Ruangrupa、Forum Lenteng這樣活躍的藝術社群過於議題導向存在批評,說這些藝術實踐更像社會運動。
NJ:我覺得藝術必須可以應用,我指的是應用於社會。藝術實踐也勢必與社會群眾對話。我們必須了解自己的目的與定位—藝術是誠實的,我們必須勇於溝通。或許某些人試圖將藝術與運動區分開來,但對我而言,這限縮人們對藝術的想像。很多事無法一分為二,有時候甚至是混合的。去定義什麼是藝術?什麼是運動?我覺得不是重要的課題,我會說不重要,一是因為當代藝術在印尼的發展越來越模糊,很難被框架;二是回到藝文實踐者身上,他們的動能為何?進步為何?藝術的生產者與生產方法已不同以往,像科技的革新,我們看到很多移工用手機直播、發Vlog,這些素材經過剪輯也可以成為錄像作品,像辦展覽。對我來說,他們在Instagram上發照片也是一種展演。
人類自己也越來越複雜,我們怎麼能去規定藝術應該是怎樣呢?藝術實踐是轉譯對大眾行為的觀察,學院並不是藝術生產的必要條件,那太菁英主義。在1980、90年代的印尼藝術圈,界線仍然分明,但現今的印尼已經不適用了。有這種想法的人是「Jadul」(Jaman Dulu,舊時代,指「過時的」)。你可以參考我對Ruangrupa創辦人Ade Darmawan的訪談 (註2),針對這個主題曾有許多討論。
WT:Kunci在藝術圈會常被看作是運動份子嗎?
NJ:印尼大學的Melani Budianta教授曾以「應急狀態」(Emergency Situation)描述1998年後的印尼,文化行動在這時代被看做「應急行動主義」(Emergency Activism)。這些行動是為了填補社會的空洞,而「應急」意味這些行動短暫與快速的特性。政治改革(Reformasi)至今20年,我們行動主義者仍在處理蘇哈托(Suharto)留下來的坑疤中。然而,填補了一個洞,其他的社會情境又會出現另一個洞,或說在被填平的空洞表面,又有新的洞自底下浮現。我們如何看待這個短暫卻不斷延長的時代?我們的存在是為了填補這些空洞,或許我們也得靠這些空洞來定義自己。我們以極度亢進的方式承擔各種角色與責任,換句話說,這就是為生命所做的奮鬥。

WT:你或Kunci的計劃好像總有對抗的對象?
NJ:這些計劃並不一定有對抗的對象,但必須保持著批判的態度。藝術圈是很傲慢的,尤其自視甚高的文學界,不開放,對藝術生產也沒幫助。是說要怎麼對抗呢?就是直接對話,我也常被他們視為傲慢的人…
WT:印尼有許多人在營造社群(Gotong Royong)、體制外教育、另類學校(alternative school)等, 2016年Kunci開啟的SoIE(School of Improper Education) 跟坊間的另類學校有何不同?
NJ:在成立17年後,我們開始思索未來,也重新尋找與社會的距離。1998年後我們試著定義自我,至今我們仍在學習如何成為自己。我在1990年代經歷特殊的學習經驗,「替代」(alternative;或另類)便是這時代的主角,或者說「替代」定義了「九八世代」(Generation 98)的我們。我喜歡用「替代」一詞因為當時無法找到定義那些邊緣、彈性、流動及有適應力的地方。我們也用「替代」來指那些正在變得狂放,同時滋長其適應能力的事物。
我從未將SoIE定位為另類學校,但我常得默認SoIE為其中一種模型。SoIE在印尼並不特殊,也沒有更酷,印尼有很多另類學校或體制外單位。不過我們想做的,是實驗並實踐較不為人知的教學方法,像刻意模仿Joseph Jakotot的方法,他強調老師在課堂中不該是權力與知識的權威,而知識應該是老師與學生合作生產。再來是「Turba」、「Nyantrik」與「Taman Siswo」(註3)。SoIE是完全實驗性,與其他另類學校不同的是,許多學校是針對不適應公營學校的學生,但SoIE是在藝術與文化的脈絡上創建,它後來比較像培訓都會地區的文化行動者。但就我所知,多數以替代教育為名的學校,師生的關係跟一般體制內教育並無太大差異,多數僅是複製既有制度,師生間的距離也類似。Kunci一開始想要崩解這樣的距離,強調彼此的溝通與協調,同時解構學校的定義,在理念上跟其他學校有極大差異。
WT:就我們討論的,SoIE的「Turba」(Turun ke Bawah;下鄉、下放至底層)從字面上暗示了方向,你怎麼回應知識圈對它的批評?
NJ:在不同社會實踐中「底層」常被理解為社會階級最低者,暗示貧窮、不安全的居住環境、持續性的匱乏感不利地位。「底層」這種特定狀態顯示「上層」的存在。我對「Turba」之(底層)見解並非如此,1950、60零年代的印尼藝術家理解的「底層」很清楚,如地理上離雅加達有多遠、多邊陲的農村或漁村。我們當然可以說自己是從上層下到底層,如果我本來就在底層,那我要怎樣下去?如果我本身就是底層的窮人,現在要下放,我該把自己放到怎樣的底層?Kunci「Turba」與LEKRA(Lembaga Kebudayaan Rakyat,人民文化協會)原初「下放」及學院體系下的「KKN」(Kuliah Kerja Nyata,實習服務)的概念確有不同;Kunci的「Turba」方法意味著以不同路徑理解環境的意願與勇氣,我們對「底層」的詮釋是多元的。就我對它的觀察,「底層」應以唯物論觀點重新定義,摒棄社會對它的既有想像。SoIE學員得探索各種抵達「底層」的途徑,並試著理解「底層」為何。如有學員成為線上計程摩托車司機,他們必須反問自己「底層」在哪?這樣因人際互動造就的「底層」又是什麼?這些提問都會在過程中浮現,而我們也得以從這些個人實踐與集體討論中獲取新知。
WT:你進駐的提案是「Archives as Migrants」,為什麼不是「Migrants as Archives」?若是針對「檔案」跟「遷徙」,過去已有很多藝術家透過建立資料庫、以移民工為主題創作來作計劃。你有什麼想法嗎?
NJ:我對台北、台灣的印尼移工研究計劃了解得還不多,但我嘗試不往那方向發展。「Archivea as Migranta」先是為了拓展「遷徙者」的概念,再來拓展並發揮「建檔」的功能。一開始我想從各類印尼移工的書寫文本引出對台北的都會地景踏查。但在進駐時開始回溯各種涉入亞洲的方法,包括我經營Kunci的經驗、Kunci做過或正執行的各種計劃、我的個人計劃及對台北的觀察。我試圖統整這些經驗去創造一種更能觸及本地動態的方法。我還無法對「Archives as Migrants」提出具體想像,但像我提到的,這些方法的動能不管是印尼與台灣、台灣與其他東南亞國家、印尼與東帝汶、印尼與柬埔寨或其他國家,會隨著場域與互動持續延展。我所認知的「建檔」是:不管身在何方,在各種不同的狀態,都可以將自己的知識體系延續下去,即「Archives as Migrants」的概念。
WT:你曾說檔案是很政治性的,怎麼回應自己的建檔工作?
NJ:為什麼會叫國家檔案或「官方的」(resmi)檔案?因為國家有其權威去建構官方檔案的模樣。我們所做的是為了干擾國家權威,建檔的權力不應只掌握在國家手上,還有許多事物也有建檔的價值。我想說的是對國家而言重要的事物,在許多人眼裡並不重要。如果說檔案是某種重要且富含意義者,那我們自己也必須思索、挖掘其重要性。對我來說,建檔是一種協商,我不希望國家是唯一能決定何為重要檔案的組織,必須有更多元的編碼模式,否則我們將被國家玩弄於股掌。
WT:你這趟連續去了兩次新文化運動紀念館;你對新文化運動好像很有興趣?
NJ:我對台灣新文化運動紀念館充滿好奇,這個博物館從文化與知識行動的維度去探究日本殖民時期的反抗運動。這使我重新省視印尼和其他東南亞國家的現況,這些國家跟台灣一樣也正抵抗殖民。對我來說它展現一種團結的時刻,讓我思索亞洲國家間串聯發展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