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ows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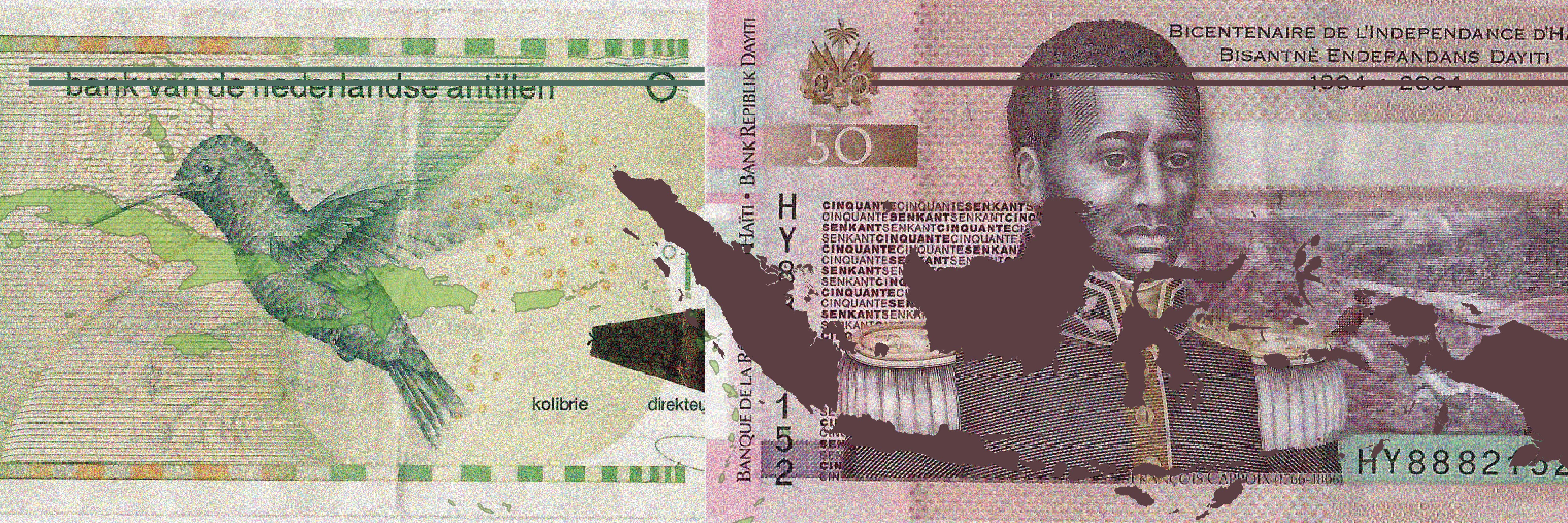
「印度」一詞作為西方的用語,最早可回溯至古希臘時期。該詞的梵語辭源或許和「河流」、或「河谷平原」有關。在希臘世界中(Hellenic World),「印度」更可能被用來模糊地指涉已知的東側邊疆之外的世界。當哥倫布抵達加勒比海諸島時,他至死堅信他抵達的陸地正是「印度」,而哥倫布的說法也不是全然錯誤,因為「印度」一詞在西方的文化語境中不僅指涉我們所知的南亞次大陸,更象徵著遠在異國的富饒之地。歐洲以其自身作為基準,往西跨越大西洋的美洲大陸被發明成「西印度」。而自歐洲繞過非洲往東航去,我們所身處的亞洲南方島群則被發明為「東印度」。
歐洲不僅以自身為軸線定義了東、西「印度」的位置,也同時阻隔了兩個「印度群島」之間的交流。人們忙著釐清自身所處的這座「印度」與歐洲之間的關係,卻往往忽略了將另一座「印度」視為參照的可能性。「東印度」與「西印度」便像是擁有同一位父親的兩個家庭,彼此的存在被父親所隔離,但卻又形成彼此的鏡像世界。歐洲作為父親就像是一個無法抹滅的幽靈,而「東印度」與「西印度」作為世界的兩端,不僅圍繞著父親而生,兩個印度自身便是父親慾望的產物—透過父親耕犁、播種於其肉身上的咖啡、菸草、甘蔗、香蕉,橡膠,並以奴隸的汗與血澆灌,成為資本主義所慾望的商品,也藉此建構了現代社會的基礎。
將兩個「印度」形容成現代世界的根基,似乎一點也不過份。本篇專題邀請了不少身處「東印度」與「西印度」的工作者,透過文學、策展經驗、民俗美學及殖民史等角度,嘗試討論自身所處的「印度」。同時在本專題透過「西印度」的提問,進而回望非洲這座爭議的大陸,導引出「詮釋者寫作計劃」的下個階段。

圖:阿姆斯特丹的「瘦橋」(Magere Brug)建於1934年;歷史照片攝於1938年(Source: Wikipedia)。(The Magere Brug before World War II in Amsterdam; source: Wikiped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