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owse
對於藝術作品的典藏來說,作品的技術物內涵與作品之意義及其表現形式的關係為何?如果「藝術」的意義不是自然而然地由藝術作品流溢而出,那麼有沒有可能改變「典藏」的方式與內容?
著名媒介理論家葛洛伊斯(Boris Groys)建議我們將美術館典藏視為是決定「現實(reality)」內容的因素。對我們來說,把「新/舊」這組區分當成思考「典藏」的首要區分,應當是在實做層面上思考藝術作品之技術內涵與典藏問題的基本切入點。葛洛伊斯認為,我們這個時代對於「藝術/藝術家/藝術作品」三者關係的看法已經不同於傳統時期(也就是葛洛伊斯所謂的「啟蒙時期」)。
傳統時期在意「藝術的起源與隨後的成功」,相信英雄化的天才藝術家,認為重要的藝術作品是人類文明的里程碑,藝術史的發展所展現的是越來越進步的人類文明,線性的編年藝術史代表著這樣的史觀,博物館或美術館單純只是承載這種史觀的空間,這樣的空間以常設展與典藏展為主要內容。不同於啟蒙時期,我們這個時代並不是「客觀的世界秩序」先於「美術館典藏」的時代,葛洛伊斯認為這恰恰是「藝術終結」論提醒我們的事情:是線性的英雄式天才藝術史的終結。就此而言,藝術並未終結自身;相對而言,藝術中前衛派所開發出來的、作為判斷標準的「新」(註1),從客觀天才的創作或發明,轉變為「只有在美術館典藏範圍外的事物才是新的」。(註1)
正是針對著「美術館典藏」而來、希望進入美術館收藏清單中,所以藝術家才想製造新的、生氣勃勃的、在場且現在的藝術作品,來爭取成為「現實」的一部份,或者說,成為「未來無法繞過的『過去』」。「藝術」與「現實」兩者間的界線的推移,並非首先是「內含於藝術作品自身的意義」的進展,而是「美術館典藏」所造成的。就此而言,藝術作品不具有其內在的固定意義,而必須在整體上被「美術館典藏」與「策展的脈絡」(註3) 所決定。或用葛洛伊斯更為直接的說法:「新」不來自「本真性(authenticity)」。(註4)
技術內在於意義架構
對我們這個時代來說,除了上述「藝術作品不具有其內在的固定意義」之外,現代藝術還提醒我們要注意「意義自身的物質性」問題。不過讓我們先後退一步,處理霍爾(Erich Hörl)對於「技術與意義」兩這關係的考察。霍爾在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所提出的「技術」問題視域中,發現西方哲學往往把「技術」與「意義」對立起來,貶抑並批判「技術」,不過他提到,海德格在1930年代透過對於量子力學與機械科學的觀查,發現在他之前的哲學往往預設了「物的物性」,但是當時的科學進展讓海德格理解到,「物的物性」所預設的「物與世界的原初關係」並不存在,不過海格並沒有繼續深究這個議題。霍爾將海德格的理論銜接上南西(Jean-Luc Nancy)的「意義史」與夏儂(Claude Shannon)的「語義學」提案,認為只有清楚地意識到「技術以框架(Gestell)的方式內在於意義」,才不至於像柏拉圖或康德一樣,將「技術」改頭換面為「理型」或人類認知的「圖示」而再引入人類社會之中,成為神秘或超驗的部件。(註5)
換句話說,技術是意義內在的組成部份,而不是從屬於意義或外在於意義的。現代藝術轉向它的「物質性」面向,恰恰清楚地說明了這件事情,封塔納(Lucio Fontana)劃開畫布的那一刀,並未解消整個繪畫史,反而是凸顯了繪畫與藝術的「物質性」層面與「表現」層面兩者「互賴」卻「不相同」的情況。
對於盧曼(Niklas Luhmann)來說,這清楚地說明了「技術不是從屬於藝術的」,他建議我們區分「藝術的『系統』」層面與「技術的『媒介』層面」兩者。「藝術」作為不同於政治、經濟、宗教、法律的「系統」,在現代社會中分化出來,為的就是在這個個體化的現代社會中,處理「個別的個體如何透過不同於語言的其他媒介來溝通」的問題;而「技術」(註6) 作為聲音、光、顏色、姿態、空間…等不同「媒介」的緊密耦合形式,具有全然不同於作為「系統」的「藝術」的發展脈絡。(註7)
為了更凸顯工業革命以降,技術以「媒介」的方式進入藝術領域中,成為承載創作的重要環節,並為我們對於典藏與技術的思考提供實做面向上的著力點,我們或許能夠進一步採用史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的「器官學(organology)」提議,將工業革命視為是「器官學的工業化過程」。(註8) 史蒂格勒將「器官」放在「宇宙學(cosmology)」的脈絡下來思考,因為他所謂的「器官」並非生物學意義上的,而是承接著西蒙東(Gilbert Simondon)的理論脈絡而來的、是「跨個體性的集體」意義上的。這樣一種集體意義下的「宇宙」,乃是從意義認知、語言使用到文化構成的「整體」(雖然是不完整的整體),而「技術」乃是所有思想與律則的構成基礎。在這個理論脈絡中,「技術」不是某種理論或學說的「應用」,而是回頭過來建構意義(包括文化)與認知方式的基礎。

史蒂格勒宇宙學意義下的「器官」,是一種組成「宇宙」的局部性(local)位置,我們將這個理論銜接上葛洛伊斯的「塑造『現實』的美術館典藏」,並將藝術作品的物質性面向理解為其「技術」面向。費奇里(Peter Fischli)與魏斯(David Weiss)的許多作品,清楚地平行於我們這樣理論,展現這個理論物質性樣貌。在這兩位藝術家的《無題(樹根)》這件作品中,他們以聚氨酯這種輕型的塑膠,唯妙唯肖地等比例仿造了一段樹根,由於禁止觸摸,所以觀眾只能從說明牌上發現這個作品並非真正的樹根。葛洛伊斯以這個作品來解釋「物質性」的作為藝術作品的隱藏內核,對我們來說,更重要的是,這個內核仰賴「技術」的支撐。
技術、保養與人造壽命
綜合上述兩個部份的討論,我們已經來到必須將「藝術」與「技術」兩者分開思考的理論位置上。就美術館典藏實務而言,這只是常識:對典藏品的日常點檢往往只在意作品在物質性或技術層面上的損耗或破壞與否,而絕少從藝術概念、創作理念、甚至策展論述來檢視作品是否有所缺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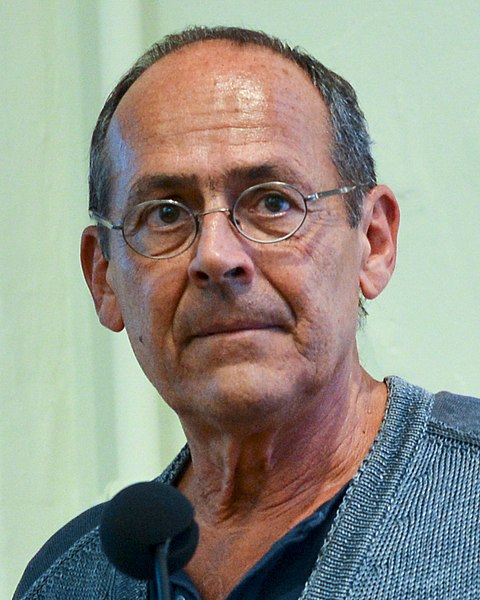
將藝術與技術分開,意味著我們可以嘗試一條與目前主流的典藏政策非常不同的激進道路,一種「媒介考古學」式的典藏理論:將每個藝術作品都視為是一個完整的「技術系統」,而這個技術系統的每個環節,也就是每個史蒂格勒意義下的「器官」,都有其各自的生命週期,甚至會死亡。對葛洛伊斯來說,當「作品」成為「典藏品」之後,就擁有了不同於現實世界的生命長度,他稱之為「人造壽命」。只要這個作品還是美術館的典藏品 (註9),美術館就會動用最大的努力,來維持這件作品的生命。不過,葛洛伊斯也清楚地指出,藝術品終究會死亡,而且是物質意義上的死亡,這樣的死亡是必然的。這個「人造壽命」恰恰是「美術館典藏」相關業務的核心,而且,正如葛洛伊斯也清楚指出的,「在美術館物件與實際物品間,其期望壽命無法察覺的差異,將我們的想像從物件的外表形象,轉移到維護、修復,以及所有的物質支撐的結構,這些美術館的內部核心元素。」(註10)
在這個「藝術作品=(媒介考古學式的技術系統)」與「人造壽命」的理論立場上,我們認為,只要在考慮藝術表現形式所牽涉的媒材(也就是物質性)效應不會因而改變的前提下,作品部件的更替可以等同於技術元件的更替。更進一步地,我想在這裡銜接上艾德格頓(David Edgerton)的技術史思考,從「使用」(註11) 而非「發明」的角度,將上述「美術館典藏/現實」兩者間的關係視為是日常生活中的「使用」關係,而非以起源的方式將藝術作品的出現類同於「發明」或「創新」。(註12) 這樣一種「使用」或「操作」的媒介考古學與技術史視角,在面對「使用中的技術」時,會考慮同時存在的「替代技術」(註13),這些可以相互替代的技術面對的是「問題的同一性」,只是在解決手段上採取不同的方案。就此而言,在面美術館典藏品時,於表現形式許可的範圍內,我們可以不再堅持於作品原來的技術選擇,因為這些「技術的無意識」或「媒介的無意識」並不在原來「藝術」的表現與展示範疇,而屬於「技術」自身的範疇。
在「使用中的技術」與「替代技術」之外,與葛洛伊斯類似的,艾德格頓從技術史的考察出發,也發現在這個技術「系統化」的時代,相較於發明與創新,「保養」與修復才是投入成本較多的部份,而且,「保養」需要完全不同於「生產」的技術知識。(註14) 就美術館的典藏實務而言,主要的業務內容就集中在「保養」的領域內,在這個技術系統化的時代,沒有人可以全面性地熟悉所有的技術系統,從從光電到影音、軟體到硬體、從物理化學到生物,但是藝術的發展越來越趨向將這些不同的技術系統都納入自身的實驗範圍內。就此而言,恰恰由於前述藝術與技術的分立,以及「保養」知識作為美術館典藏相關人員在實務上最主要的技術性知識,但卻沒有任何人可以全面地掌握所有這些知識,所以本文認為應該將保養業務視情況外包給不同專業技術公司或個人,而只在美術館內部維持有限的、熟悉這類知識之分類並具有基本操作知識的人員,一方面減低美術館「非藝術性的組織肥大」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能夠因應不同的技術生命週期,隨時透過保養與修復維持作品在物質與技術層面上正常運作與展示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