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owse
許家維參與2016年台北雙年展展出的〈神靈的書寫〉是一件錄像裝置作品。展廳中央的投影螢幕分成兩面,一個投影面的內容是許家維請示鐵甲元帥,是否能夠允許他拍攝一部有關元帥的影片,影片內容正是他對於元帥是否允許之祈求,以及跟元帥解釋另一部動畫的處理方式的過程;而另一個投影的內容,是以3D動畫的形式來處理元帥府所座落的地理位置、空間樣態,以及輦轎的動態。這兩個投影面分從相反方向投影在同一個投影幕上,旁邊兩張影像輸出的內容,一張是站在拍攝之綠幕前的元帥的乩手及桌頭團隊,另一張則是動畫繪製的元帥府的空間地形圖。
對於〈神靈的書寫〉這個作品,藝術家特別強調「行動」的面向。許家維提到,這個拍片的行為「是個真實的行動過程,我透過把我自己的角色放進來,然後跟鐵甲元帥,我覺得有點像是建立一種當代藝術跟民間信仰的關係」(註1)。對本文來說,藝術家所提到的「真實的行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藝術家之所以強調行動是「真實的」,是因為藝術家與我們多數人分享了一個共同的預設:影像的生產與放映並「不直接」產生改變社會的效果。這個不直接產生效果的反應,甚至被藝術家理解為「藝術」的特質,所以藝術觀賞並非「真實的行動」。
就此而言,藝術家不滿足於只以一個藝術家的角色參與到影像生產的過程之中,還「扮演」了「信徒(問事者)」的角色。(註2) 從宗教的角度來看,一個人之所以被稱為「信徒」的基礎在於「信仰」(註3),單純信仰就足以直接對信仰者社群發揮效力,而不需要透過圖像或影像的媒介。然而,就〈神靈的書寫〉這個作品所欲驅動的觀眾群,主要是將作品認知為藝術而非宗教性神聖影像的觀眾。藝術家所謂的「自己的角色」,其實是這樣一種「從藝術視角出發來理解事物與世界」的立足點所撐開的存在方式。這樣的藝術性的存在方式如何要能夠在宗教性的神聖空間中找到屬於自己的位置?〈神靈的書寫〉中對於過程的拍攝是對於宗教儀式過程的「紀錄」嗎?
表演而非記錄
從藝術家的訪談中我們知道,〈神靈的書寫〉的出發點首先並非「敘事」,而是「行動」。誠如前述,行動在這裡意味著實際能夠引發下一個行動的效力,對於〈神靈的書寫〉而言,而這個行動鏈最終所指向的,是作品的完成。不過,正因為這個作品必須面對來自宗教神聖性的要求,所以「行動鏈」必須跨越「宗教」與「藝術」兩個脈絡,作品的完成同時就意味著神聖性的達成,也就是必須滿足由超驗觀察者所下的指令。〈神靈的書寫〉是怎麼同時滿足藝術與宗教兩種行動迴路的呢?
藝術家透過將自己放到被拍攝的內容中,同時在「觀察者」與「創造(創作)者」兩個層面上都製造了角色的分裂。在「觀察者」的層面上,許家維的角色分裂成「宗教儀式的觀察者」與「從藝術立場出發的觀察者」兩者。宗教性的觀察者可以選擇參與宗教儀式與否,而從藝術立場出發的觀察者則必須採取與宗教截然不同的態度,拉開與宗教的距離,製造以不同立場(在這裡是「藝術」)來觀看宗教儀式的方式。然而,只是在「觀察」層面上爭取到「(藝術與宗教兩者的)距離」,只獲得一種美學層面上的「空間」(註4),頂多只能「記錄」並「旁觀」(甚至「反省」)宗教,卻尚無法支撐一種美學的「行動」。因此,藝術家在這裡還為我們提供了「創造(創作)者」的層面上的分裂,方能完成這樣的過渡。
就「創造者」層面來說,雖然在宗教儀式上,只有鐵甲元帥才具有神聖的效力,然而對於在藝術脈絡下欣賞這個作品的觀眾而言,佔據第一人稱創作者位置的,同時有鐵甲元帥與許家維兩人,創作的行動鏈由鐵甲元帥與許家維接續完成,此時動詞意義下的「創造」透過滲入「生產(produce)」的語意而弱化了「創造」的神聖性,從而能夠較為輕巧地滑移到「(人造的、美學的)創作」這個語意上,神聖性的創造與美學性的創作兩者,就藝術脈絡而言,就穩定在「創作」這個語意上。(註5) 在「創作」與「行動」的交會點,我們遇到的不再是「記錄」而是「表演」(註6)。
表演者與秩序形象
然而,我們絕對無法繞過的問題是:到底是誰在表演?是鐵甲元帥,許家維,還是其他的事物?讓我們把這個問題的預設脈絡再說地更明白些:對於那些在美術館空間中觀賞〈神靈的書寫〉的觀眾來說(而非芹壁村裡觀看宗教儀式的居民),到底是誰在表演?如果如其中一面投影內容,藝術家都已經將自身放到拍攝的影像內容之中,或者如同另一面投影內容,只有3D動畫繪製的、元帥府前的輦轎在動作,那麼在這麼多不同的敘事脈絡中,觀眾所面對的表演者是誰?
為了確立這個表演者,我們必須分成兩個部分來加以探討。首先,對芹壁村的居民而言,在請示元帥的宗教儀式中,鐵甲元帥「既顯靈又不現身」。作為一個宗教儀式,我們看到的是芹壁村村民所抬的輦轎受到來自元帥的力量,傳達到抬轎者的身體,迫使不同的抬轎者各自以不同的動作方式行動。整體而言,輦轎表現出的是個不受抬轎者意志控制的自動機(automata)的形象,然而卻能透過輦轎對抬轎者施加行動範圍與行動方式的限制。對於宗教儀式的觀眾來說,這是一種視覺層面上的政治操作策略,透過自動機的形象來替代宗教—政治—社會體制的說明:(註7) 自動機並非自動機,而有一個「(觀眾)看不見卻實際上正在顯靈」的號令者調動扛著輦轎的居民來達成號令者希望完成的事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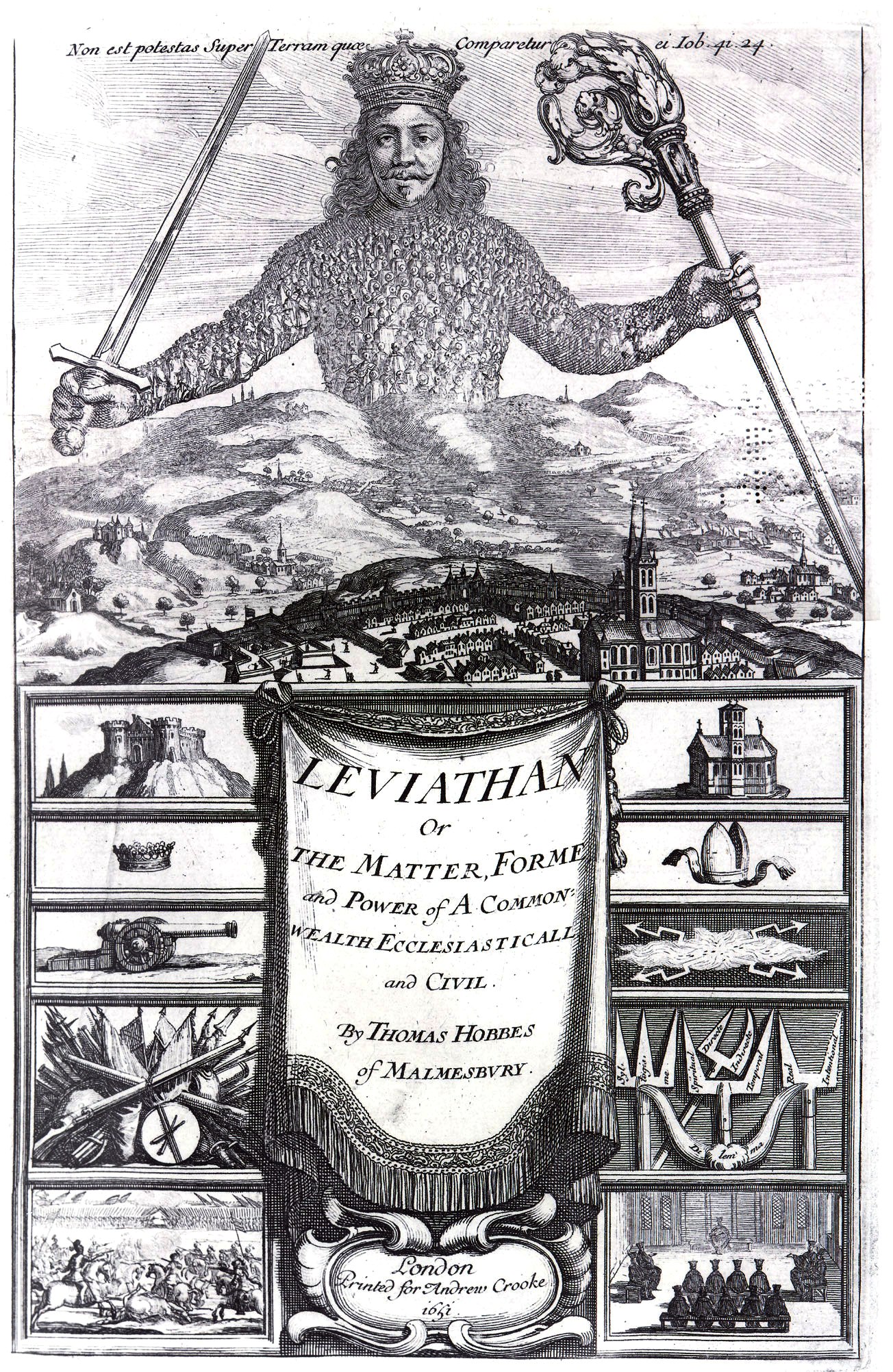
就此而言,「力量」分成兩個層面被理解:在「形象」政治的層面,以輦轎為媒介,將「在場卻未現身」的神靈與「現身卻不受自己控制(也就是:「自己」不在場)」的抬轎者縫補成一個因矛盾而具有張力的形象;在「效果」的層面,彼此受到牽制、不同方向上發動的抬轎者身體讓「力量」以其非一致性的狀態,在輦轎結構的限制下生產出最基本的「痕跡」來,並經由桌頭對痕跡的解碼,而轉化成「秩序」的效果性宣告。在這個場景中,表演者是輦轎及扛轎的村民,元帥則是因為總體秩序之效果而被推斷存在卻不在場的在場者,換言之,元帥是「秩序」的形象替代物。
對於北美館展場中的觀眾來說,〈神靈的書寫〉作為一件藝術作品,有著類似於前述宗教儀式的「表演者/秩序之形象」的結構,表演者包括兩件投影與兩件攝影輸出,影像敘事的發展以及展示的空間結構都是表演的不同環節,而總體秩序所需的形象,則由藝術家刻意安排的「綠幕」來充當。
神界與後設控制
「表演者/總體秩序之形象」在宗教儀式中以「輦轎及扛轎的村民/鐵甲元帥」的方式呈現,而在〈神靈的書寫〉中以「投影影像及攝影作品/綠幕」的區分滿足了同樣的差異。正是在「表演者/總體秩序之形象」這組差異的結構下,我們才真正地涉入藝術家之所以以3D動畫的方式加以描摹的空間。
為什麼要用3D動畫來處理?對於藝術家來說,「神界好像不屬於任何地方,是一個虛空的空間」並能夠與3D的動畫世界產生一種對話關係。不過,承接上述的討論,我們必須把「動畫的內容」與「3D數位動畫系統」區分開來。〈神靈的書寫〉中的3D動畫投影,是以鐵甲元帥廟及其地理空間位置為原型所做的3D建模過程,建模過程中輦轎在行動時,藝術家並未如實際起乩的宗教儀式一樣,將抬轎者一併繪入,反而讓輦轎懸浮在虛擬空間之中,所有現實世界中的人類行動者,在3D建模時都不存在,換句話說,前述現實世界宗教儀式中那些「現身卻不受自己控制」的抬轎者,因其不具「秩序」效果,而在這個3D動畫虛擬世界中消失。
很明顯的,藝術與民間宗教,或說3D動畫與神界之間的對話關係,正是放在這種「總體秩序」的考量下,方才展現它們兩者之間強烈的相似性:元帥作為秩序的形象,是一種總體性的後設補遺,為的是將整個宗教儀式收束到唯一一個動因之上;與此類似的,3D動畫系統作為一個對現實建模的工具,雖然有別於現實,卻能夠將現實縮小化為模型:
模型的縮小化製造了一種心理上的過剩,這種過剩從它那方面來說沒有擺脫一種有心靈暗示能力的物理性,這種物理性來自模型自身。(註8)
元帥與3D動畫繪圖系統兩者為(影像)敘事所打開的空間,正是這樣一種非物理性、卻為物理性所限制的心靈空間,這個空間作為一種「秩序之形象」的空間,是為了後設性的控制而存在的。或許我們可以這麼說:這是一種為了敘事而產生的系統層面上的奠基,〈神靈的書寫〉的敘事正是在這個基礎上才得以開展。